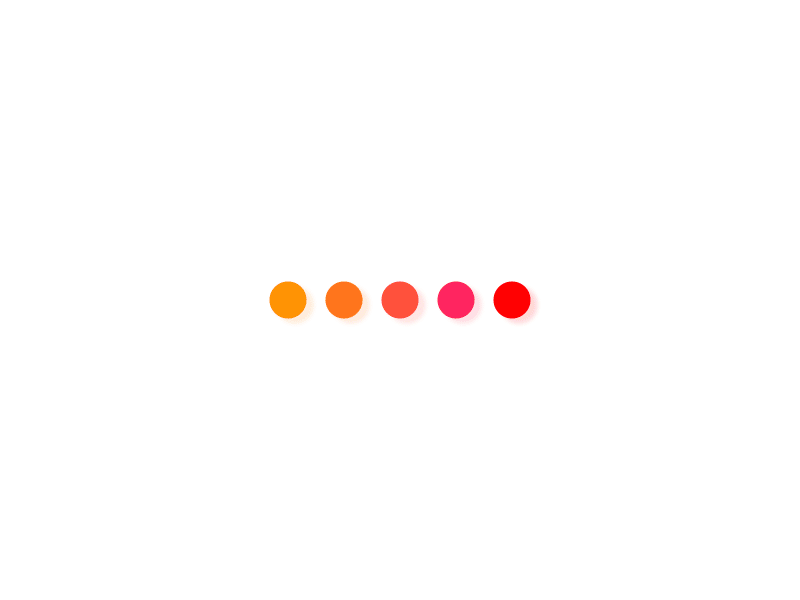我的村庄
张娜
清晨领着女儿坐在客厅沙发上玩耍,阳光照进窗户撒在女儿粉嘟嘟的脸庞上,女儿咯咯笑着扑进我的怀里,感觉这世间万物的一切以及一尘不染的风景都不及眼前的女儿。正当我们陶醉地沐浴在阳光里时,妈妈打来了视频,引逗女儿的同时又聊起了乡里的房子要不要拆的问题。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家里有任何事妈妈都习惯了找我商量,每天电话视频比之前格外频繁了一些,被特别需要的这种感觉真好。我知道妈妈内心深处还是舍不得拆,因为乡里的房子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见证了爸爸妈妈最好的年华。视频挂了以后,我的思绪也随着秋风飘到了小时候。
我出生在一座名叫阿家庄的小村庄,她位于甘州区安阳乡明家城村东面,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有人说“故乡,是游子用谷子酿造出来的陈年老酒,搁置年代越远,存放时间越长,酒的味道就越醇香”。我觉得我的村庄就像是一道色香味俱全而又永远吃不腻的佳肴,也是儿时记忆中的片段,越来越理不清头绪,越来越剪不出完整的画面。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小时候的我,是由老太(爷爷的妈妈)以及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特别是老太,对我格外疼爱一些。从我记事起,老太就住在老房子东屋的里屋,外屋则有爷爷奶奶居住,北屋是叔叔和婶婶,西屋则是我们一家的,因为爸爸妈妈长期在外东躲西藏的想方设法生弟弟,所以西屋大多数时间都空着。那时候的我超级喜欢和老太待在一起,老太的里屋布局陈列都特别简单,屋里就摆放着一组柜子,而我最喜欢的是狭窄的炕尾放着得那个深红色木头箱子,经常挂着一把不太安全的铁将军锁着。据老太说那个木头箱子是她唯一的陪嫁,我的老太户口本上写着出生于1926年,具体生日她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她知道自己15岁那年就嫁给了我的男老太。
老太的那个木头箱子就是我童年时期的百宝箱,每当老太悄悄地把我叫进里屋,我就像只饿了好几天等着被投喂的小动物,留着口水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太从大襟布衫里面的口袋掏出钥匙,听着锁开的那一瞬间,我格外兴奋。老太会从木头箱子里变出各种各样零食:比如香蕉、苹果、果丹皮、唐僧肉、罐头之类的来抚慰我这个留守儿童的幼小心灵。那个红棕色的木头箱子和我就是老太的一切,我陪着她度过一个又一个漆黑而又孤单的夜晚,她陪着我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美好而又快乐的童年,正是因为有了老太以及爷爷奶奶的偏爱,我才不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小时候的我基本属于放养,每天和村庄里的小伙伴疯来疯去。春天跟着爷爷奶奶坐在那个木耙上灰头土脸的耙地,夏天去涝池(农村的蓄水池)里摸鱼或者到空旷的天地里放牛,秋天去村庄的杏树林里摘杏子,冬天则扯着嗓子在村庄里在涝池里滑冰。我们村庄的那个涝池,是我儿时的玩乐天堂之一,那里视野开阔,我最喜欢爬上涝池墙骑在上面眺望远方。
春天万物复苏,涝池里的冰块开始慢慢融化,涝池最北面和我家老房子的南墙根总是最先被春天临幸的地方,那里黄绿色的小草芽总是最先来庄里报道。等夏天到了,冰雪也完全融化了,整个涝池里水面波光粼粼,水面外绿意盎然,即便那是一汪死水,涝池里面整天都笑声不断。有大一点的孩子拿着用竹竿自制的鱼竿在聚精会神的钓鱼,有的坐在阴凉的地方看书,还有的只穿着裤衩组团赤脚下水摸鱼,有的在用汽水瓶捞蝌蚪,还有的拿着小铲子组队挖蕨麻,周围还有几只觅着吃草的羊和牛。
下午的时候会有成群的牛群或者羊群争先恐后地进来喝水纳凉,特别是牛群总喜欢去涝池最中央喝水,等他们喝足了,就会气定神闲的站在涝池中央,悠闲的用尾巴驱赶蚊虫,直到主人往外赶才肯离开。到了盛夏的晚上,涝池里也热闹非凡,各种虫鸣声夹杂着蛤蟆声此起彼伏,奏着一曲又一曲的交响乐,似乎在控诉那炎热的夏天。那时候夜晚的村道,每走几步路就能碰见几只蹦跶的癞蛤蟆。
去年碰见了一位朋友,他家在城郊村,他的孩子从小乡里长大,某个周一早上他突然被孩子老师请到了办公室,原因是他的孩子公然在学校里卖癞蛤蟆和蝌蚪,听说生意还异常火爆,还有下一周预定的。我老公直夸他孩子有生意头脑,我不禁想了想现在我的孩子也没见过蛤蟆,更别说蝌蚪了,我的孩子见了肯定也会买吧,买不上肯定也会预定吧。
秋天的捞池就有些萧条了,因为我的村庄靠近祁连山,秋天凉得格外早。这期间除了有牲畜进去饮水,依然就是孩子的欢声笑语不断传来,他们在过家家,玩小水沟也乐此不疲。冬天的涝池更是我们的天堂,等涝池水面冻瓷实,就撒欢在上面滑冰,能玩上一整天。中午和下午你如果坐在涝池墙上,时不时就会看见有大人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来边骂边来找自家小孩,多半都是因为玩的忘了回家吃饭或者写作业之类的。如果下雪了我们就会在冰面上打雪仗,等玩累了,就会捏一个雪球找一个有太阳也有细土的地方去做一个土球,就是在雪球外面不停地滚土,等土滚的足够多,放在太阳底下,里面的雪球就会融化,然后在土球上戳个小洞,把雪水引出来,然后放碎石子进去,把那个小洞封住就成功了。那时候我们经常蹲在涝池墙根下比赛谁弄得土球多,谁弄得又大又结实。
我们村庄有一大片杏树林,等杏花开了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杏花的香味,等杏花落了刚结了果,我们就开始爬上树吃杏子,即便酸得口水直流,还是不停地往嘴里塞。杏子长大一些,杏树也绿了起来,除了在杏树林里耍猴的我们这些孩子,还有周围地里干活的庄里人。干累了,他们都会提着腰食来坐到杏树底下歇歇脚,解解乏。等秋天到了,远远地就看见杏林黄橙橙的一片,仿佛在诉说着秋收的喜悦。
这个时候的杏树林是最热闹的,每天从早到晚路上都能看见拿着竹竿,提着袋子往杏树林走的身影。除了吃,送人,有些人还晒杏干,挤杏核卖钱。这时候的我每次都是拿着竹竿上树敲打杏子的,老太以及爷爷奶奶就在树下拾,等把拿来的袋子都装满了,爷爷就推着独轮推车,我往上面一坐就回家了。我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杏子,应该与我的村庄那片杏林有一定关系吧,我喜欢爬上杏树的那种感觉。
小时候的庄里,进城的寥寥无几,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居住,每到夏天大人下地回来,都会提溜个小凳子,端着碗,坐在自家门口纳凉吃饭,和邻居谈笑风生。那时候的我们家里如果没大人做饭,可以随便从街头蹭吃蹭喝到街尾,不管是馍馍还是饭总会吃到,绝对不会饿肚子。等我们上小学了,家家户户开始通自来水了。记得那时候路上都在挖自来水管道,庄里有人的猪跑出来掉了进去,几乎整条街的人都过来帮忙了,齐心协力喊口号,用劲把那头很肥的猪抬了上来。如今那种邻里之间的和谐友爱我再也没有体会到过。
我家老房子在十字路口,村上有啥通知通告之类的都贴在我家老房子墙上,再加上前面没有遮挡物,光照十足,所以我家老房子南墙底下就是冬天闲聊娱乐休闲的地方。女的拿着鞋垫,布鞋或者毛线等边聊天边干手里活;男的有些在脸红脖子粗的下象棋,有些靠着南墙根、手缩在袖筒里聊庄里庄外的新鲜事和八卦等。即使后背靠了一后背的土,仍然毫不在意地继续谈天说地。
上六年级了,得去乡政府那里。由于路途较远,每周末才回家。其他时候还可以,就是下雨的时候,回村庄的那条道就会泥泞不堪,特别是回校的时候,干净的衣服鞋就会被弄得满身泥泞。有一次回家和庄里一位嫂子坐到了同一辆班车上,她刚打工回来,提着皮箱,由于雨下得大,到阿家庄的人又只有我们两个,司机觉得送一下划不来,就让我们在村委会那里下车了。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相互搀扶着,滑行着回到了家。她到家门口皮箱轮子掉了两个,浑身都是泥水,我到家门口浑身湿透,校服上也全都是泥水。她当时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这个阿家庄子我真的一步都不想踏入。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我的村庄开始有了一种抵触的情绪,我迫切地想逃离出去。
等上初中的时候,寒假还可以,无非就是做做饭,洗洗衣服。特别每个暑假就是农忙的时候,等麦子快黄的时候得跟着妈妈割埂草,那时候我们的地埂上基本全是芨芨草,割得胳膊撕拉着疼,晚上能被疼醒。等把割得埂草晒干再上房顶堆好,收拾完以后麦子,大麦等基本就黄了,都来不及喘口气,又接着开始收麦子等。那时候妈妈怕早上起的迟了,太阳出来麦头容易折,所以收麦子时候就得凌晨三四点起床,趁着有露水,有湿气,还有就是不晒,那时候头上戴着灯,撅着屁股,勾着腰就开始和太阳赛跑。
等你累了,歇息得时候你抬起头来,就会看见周围田地里星星点点的全是移动的灯光,就像是散落田间的星星,很治愈,很美好。等麦子割完就开始捆麦子,这时候芨芨草就会有大用处,老太就会坐在家里一天像拧绳一样给我们打芨芨草腰子。等把麦子用拖拉机拉到打麦场的时候,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不会堆那个麦垛,再说推卖垛是个技术活,也是重体力活,我妈妈和奶奶都拿不下来。麦垛的底座要大更要稳,这样基础才稳固,风吹雨打的时候不容易倒。
在庄里我爷爷是装麦车,堆麦垛的高手,好几车麦子在爷爷脚下最后成了一个个瓷实的圆锥体,馒头型。等麦子全部收回来,打麦场四周已经平地崛起了好几个高傲的麦草垛。等天气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可以打场了,清晨早早起床把麦垛拆开,芨芨草腰子用镰刀砍断,顺着一个方向把麦子摊平在打麦场上,然后爷爷就开着拖拉机,后面带着石滚或者铁滚压着摊平的麦子转圈,反反复复一直到麦子下来,接下来就顺着风的方向把打下来的麦子蹿成一堎,开始用木掀扬场。爷爷是庄家地里的一把好手,等新鲜干净的麦子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爷爷总喜欢在麦子堆里躺一躺,看着天空的飞鸟流云,这是他一年挥汗如雨,辛勤劳作的回报,即使爷爷被太阳晒得黝黑,手被麦芒扎的粗糙,我想躺在麦子堆上的爷爷仍然是是自豪的,喜悦的。
小时候的我不需要被当成劳动力来干农活,基本就是去打麦场上看着晒麦子,放一只牛和两三只羊。当小时候的我被麦芒扎红肿一片的时候,爷爷总是让我站得离麦子远一点再远一点。那时候我最喜欢吃奶奶烧的麦子,麦子刚上面还没有黄的时候烧着吃最好,现在已经十多年没吃过烧的麦子了。
等整个麦子、大麦等都收拾完了,大人们开始收胡麻等迟一些的农作物,我则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去放牛羊,那时候一起的小伙伴很多,我们最喜欢在地里烤土豆吃。我们分工明确,有刨土豆的,有拾柴火的,有看着牛羊吃草的,最重要的那个孩子则用大小适中的土块垒烤土豆的炉子,等用拾来得柴火把那个简易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炉子烧的通红的时候,我们就把刨来得土豆扔进炉子里,然后让炉子倒塌,盖好等半个多小时土豆就熟了,不知道那时候的土豆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是庄里种出的土豆好吃,那个炉子里烤出来的土豆格外香甜软糯。离开村庄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土豆。
等我上高中了,爸爸妈妈进城打工了,我也就周末偶尔上去一下,看看老太和爷爷奶奶。高三那年,92岁高龄的老太安详地离世了,再后来爷爷奶奶也相继离我而去,我就更不怎么去乡里了。现在成家了,有了孩子几乎就不上去了。如今庄里的道路也硬化了,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然而庄里却几乎没几户人家居住了,一直没有离开就是那几位年迈的老人。
村庄涝池也干涸了,杏树林也因为推地而不复存在了。今年秋天因为爸爸,让这个死寂沉沉的村庄着实热闹了一回,悲壮而又嘹亮的唢呐声划破了宁静的村庄,那些好长时间不回庄里的街坊邻居纷纷前来吊唁爸爸,等我们把爸爸埋在秋天里,这个村庄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我领着孩子把小时候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一把锁,街头巷尾能碰到的人也寥寥无几。
如今我们的老房子屋顶也塌得塌,墙也倒得倒,院子里也杂草丛生,就中间菜园子有邻居大妈种的菜还倔强地挣扎着。有了弟弟以后我们就从老房子搬出来新建房子了。我们新建的房子在庄里的西面,如今我们整个庄子因为被政府列入了地震带,需自愿报名拆除,退出宅基地,房子留着感觉没多大用处,拆除又有万般的不舍。别说妈妈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这两处房子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儿时的快乐。那一砖一瓦都是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用汗水换来的,那时候过年,由于我舅舅姨妈众多,所以得置办好多年货,爸爸推着拉拉车载着欢呼雀跃的我们去置办年货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如果房子全部拆除了,我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理由了,除了每年回去祭奠一下那些世去的亲人。这些年,村庄一直在那里,而我却离她越来越远。虽然出嫁把户口也迁了出来,但是骨子里一直觉得自己是阿家庄的人。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愿我们都内心山河壮阔,始终相信人间值得,等我懂得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的时候,那一片杏树林,那一汪死水,那一垄田地注定我再也回不去了。
( 作者简介:张娜,甘肃张掖甘州人,1992年出生,一名基层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喜欢用心记录生活点滴,始终相信人间值得,万物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