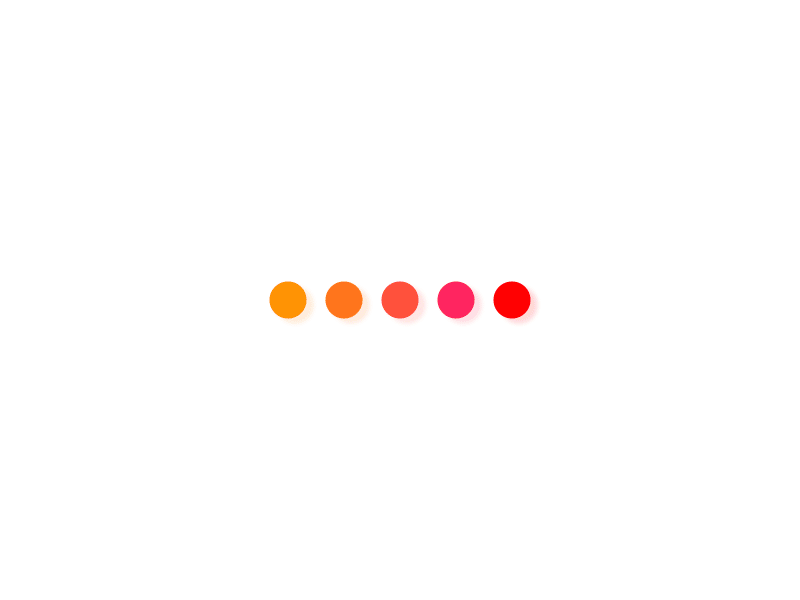大门一关,李勇生要隐藏起名字和年龄——包括他是一名盲人的事实。
这里与外界隔绝,他的身份是一串工号,职责是劝人活着。出了这扇门,他们在电话里聊起的一切,都将被秘密掩埋。
“希望24热线”,400-1619995,谐音“要留、要救、救救我”,一条专门面向企图自杀、有抑郁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热线,全年24小时无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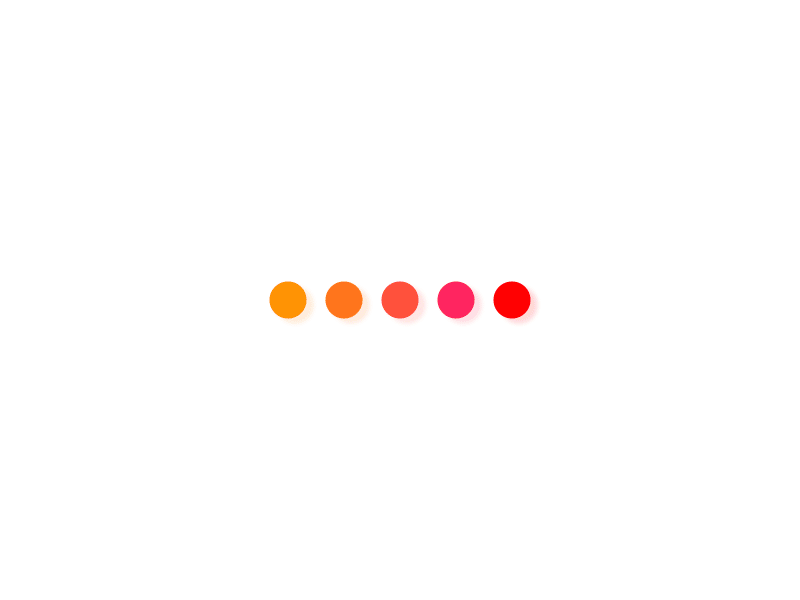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杀已成为15岁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仅次于道路伤害,每年有近80万人死于自杀。
李勇生是天津接线团的团长,也是国内第一个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接线员。
李勇生做了一个比喻:有自杀意图的人,会穿过一间间黑屋子,最后抵达灰暗的迷宫,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但在每次进入下一个黑色房间前,他们都会向外释放求救的信号。
热线是最后一道生门,李勇生要做的,就是在系统崩塌瓦解前,建立支撑点,做最后的挽救。“做他们的朋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李勇生在接听来电。图片来自《三月风》杂志
01 角色
李勇生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这是视神经萎缩留下的痕迹。一位给他拍过纪录片的记者说,他戴墨镜的样子,像日本导演北野武。
在深夜的接线室里,李勇生确实像一名导演。工作前,他要把门窗紧闭,保证安静氛围,方便进入角色。他在众多场景里穿梭,每通电话结束后,他需要时间,在大脑里进行角色转换。
晚上6点,李勇生叩开接线室的大门。这里位于天津一处写字楼内,十来平,两部电话,两人值班。“你打来电话,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说,我陪你聊天,咱们共同面对,好吗?”
自杀干预将企图自杀的人群分为4类,7个等级,26个级别。4个等级分别是轻度、中度、重度和急迫。“面对学生,我通常扮的是家长,如果是校园问题,我会扮演老师,职场白领打来的话,我就演同事。”
拿起电话,李勇生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接着听对方气息的变化、停顿时间、声音高低。5分钟内,李勇生能判断出危险等级,迅速建立一套干预方案——在此前的1000多通高危来电中,他的成功率达90%以上。
“基本聊5分钟,我就知道我能帮助他,没问题。他能投掷出求救的信号,我就知道,这人能救回来。”李勇生说。
他记得一个凌晨的电话。来电的是个女孩,李勇生听出,电话那头,有车流声,风声很大。他迅速判断出,这是一个高危来电——女孩可能在马路边或高架桥。
情况危急,李勇生调高了声音,音量与嘈杂的背景差不多大。事情在他的预料之中,女孩站在大桥上,准备往下跳。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抓准时机:“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我想听更多,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吗?找一个车辆少,能避风的地方,咱俩好好说一说。”
连线半小时后,女孩来到距离大桥200米的公交站。一个小时后,女孩听从了他的建议,回了家。“当她能和你诉说心里话的时候,危机的大门基本已经关闭了。”
李勇生近照。图片来自 Figure 视频
每一通电话,都是一次漫长的拉锯战,反复地在希望的产生和破灭中拉扯。
李勇生能体会对方的状态:“他走到这一步,不知道深思熟虑多长时间,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任何的信念系统都没有了,他只想结束生命来获得解脱。”
他要做的,就是建立“拉力系统”,建立支撑点,打开对方的心结。“能打进电话的这部分人群,他内心还保留着一些对生的希望。这是他们的求救信号,他们还在挣扎之中。”
李勇生有自己的方法:说话时不打断对方,让对话一直延续。与对方情绪同步,琢磨对方的需要,抚平对方的焦虑。“他说出这句话,可能是求石问路,我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说完后,我必须连接上他的话,给他帮助。”
这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技术不熟练,一句话刺激到他,不但不能将他拉出来,反而会激怒他的情绪,让他的心理产生瞬间剧烈的波动。
“尤其针对想自杀的人,他最怕的是一种负担,你可不要死啊,你死了以后你妈妈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他最怕听到这些。”
02 盲人的世界
盲人眼前的世界,并不是永恒的黑暗。
李勇生从事自杀干预接线员,已有7年的时间。谈起初衷,他说,既是助人,也是自救。“对方的包袱卸下后,我的包袱也卸下了,虽然我看不到,但感觉心里面是亮的,天空也是亮的,一切就不一样的感觉。”
他善于捕捉情绪变化的信号,像独独在夜里出航的船,面对漆黑的渺渺大海,总能准确判断出海浪的方向。但人无法四季在纯粹的黑暗里生存,即使他是盲人。成功挽救一个生命的感觉,难以用言语形容。
李勇生能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有时,黑夜也不是空洞的黑。他去盲校做过调查,即便是先天全盲的人,眼前也不是漆黑一片。他认为,这是受情绪调节的原因。
“即使没有光感,长时间受想法的强化,他会在脑海这种产生‘亮’的感觉,因为这样会让他感觉舒服,会让他没有压迫感和窒息感。如果在脑海中只有一片黑暗,时间长了,内心再强大的人,也走不出来了。”
李勇生40岁了,但他所有的图像记忆,都停留在10岁以前。失明几乎曾经将他的生活连根拔起。
他现在还会梦见,失明前度过的那个春天。村里有绿皮火车,路上有一些笨笨实实的卡车,车顶插着天线。家乡有一排垂柳,河边有一片青草地,树木发了嫩芽。他再未见过那样浓郁的绿色。
如今,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消散,他记不清了,连梦境也模糊起来。
李勇生近照。图片来自 Figure 视频
失明前,李勇生是村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10岁那年,他在雪地玩闹,被东西绊倒,脸扎进雪地里,眼球撞上路中间的“铁疙瘩”,一块地泵。雪地上落了血滴,他用手一碰,意识到,两只眼球破了。
路上雪厚,车子难走,去大医院要很长时间。父母带他去附近的医院,做了眼球缝合,没多久就出了院。有亲戚叹息,挺好一孩子,这辈子废了。“我听见这词极不舒服,我怎么就废了?”
李勇生常常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脑袋上像箍了一顶“铁帽子”,他总不自觉地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变得沉默,不似以前活泼,爱待在人少的地方。
他对声音愈发敏感。他判断天气,依赖的是鸟儿的叫声。天气好时,麻雀叽叽喳喳,天气坏时,鸟儿扑簌簌地乱飞,他想可能有一场大雨。他甚至能通过声音,判断马路的宽窄。
李勇生仍记得12岁发生的事情。他和朋友去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拔菜,园子主人见后,只打了李勇生。“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想来想去,为什么欺负我?就因为我看不见,就因为我是累赘,我不行了。”
脑袋上的那顶“铁帽子”,心里的疙瘩,都被一团火烧没了。“我不能这样让别人看不起,我长大了,一定不让别人说我是废人,一定活好了,还要真正活下去。”
叔叔给李勇生买了一台收音机,他靠声音和世界发生连接。他听相声评书,也听心理访谈,他知道,盲人能上盲校,学按摩,学吹打乐,又有了希望。
有次,他拨通了节目热线,一名心理学专家正在讲课。他问,我以后该去干什么?专家说,你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这很适合你。心理咨询对他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词。
从盲校毕业后,李勇生做起了盲人推拿。有天,他听说残联要举办针对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个城市只选两三个人。李勇生被选中了。后来,他顺利考到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
有次,他去长沙参加心理学的课程,知道长沙建了希望热线。“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眼前一亮。”
2015年,天津也要办希望热线,李勇生立即去报了名,成为天津首批热线志愿者。
李勇生和全家人一起旅游。图/受访者提供
闲暇时,李勇生也会想,如果没有失明,他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能会去参军,或钻研一门学问,搞创新发明。“因为意外,才走进了这个行业。既然如此,咱别的也不擅长,只会心理咨询,如果能帮助到别人,那是最好的。”
他时常感到,他与电话那头的人,处于两个世界。
在那个混乱失序的世界里,最初,他觉得自己像是村长,什么事情都帮着解决。后来,他更像侠客,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如今,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帮对方理清行动的线头,做力所能及的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03 一场对人生的模拟
听过成千上万个故事,李勇生发觉,这些相似的情节,有着人生阶段的共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挪移重现。
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老人打来的。老人年迈,常年独自生活,身体不好,当下被卖假药的骗了,不想活了。
他发现,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他们寂寞,孤独无助,多数时活在回忆里,抱有对未来的恐慌,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心理问题。
“相对而言,老年人好干预,只要让他感觉有人在和他聊天,说什么都支持,类似‘大爷说得太对了’,‘就这样没错’,让他感受到认同感,就会慢慢恢复过来。”
李勇生还遇过欠了巨额赌债的中年失意者。对方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药,准备喝下去。他给希望热线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让别人引以为戒。
李勇生成功劝阻了男人。一个多月后,男人的家属给热线打电话致谢,李勇生听接线同事说,男人已经走出了阴霾,他激动地围着椅子转圈。
他说,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而言,最基本的准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都支持和尊重他,让他感受到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关注。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要义,“必须让他感受到,我在听,我在关心,不论说什么我都能接纳。”
在听到孩子的烦恼时,他最容易动情,沉浸在对方的痛苦里。
现实中,李勇生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李勇生还记得,一个13岁的男孩,单亲家庭,父亲嗜酒赌博,男孩总是担心受怕。一个孩子饿着肚子,又怕父亲打人,又担心父亲不回来,他该多么孤独啊。李勇生想到自己的孩子。
接完电话,他站起来喝了一大杯水,出去走了一圈,大脑放空一会,才能从角色里出来。
离开接线室后,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到现实里来。
一路走去,他能听见车子的引擎声,有司机按着喇叭催促前方的车辆,街边小贩在叫喊。这些声音带来生活的实感。
但并非所有接线员都能瞬时走出来。那些困苦的情绪有时会缠绕着他们。一些感情细腻的接线员更为困扰,有人常常担心,他的困境有没有解决?他有没有再次自杀?他家人怎么样了?
“他天天沉浸在这个问题里,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最终也是有一部分人群不干这行了,因为太容易动情。”
这些痛苦也滋养了李勇生,使他对苦难有了预设。
“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过了这样那样的故事,需要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就跟打疫苗一样,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很自如,甭管过去未来,一切都是人生的反复模拟。”
04 解困
他发现,打给希望24热线的电话逐年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接听来电达39.4509万通,青少年来电占比40%,其中有5000余高危案例。
起初那些年,李勇生值班时,常常只有四五个电话。现在,电话几乎是无间断的。“这还是能打进来的,90%以上的电话是(占线)打不进来的。”
来电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学生占比最大。李勇生遇到最小的求助者,只有11岁。
需求量成倍地上升,与此同时,接线员却流失严重,十分紧缺。
据希望24热线数据,2012年热线在上海建立后,为保证专业性,希望热线要求,接线员需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或参加《心理危机干预实操技术》培训,经过培训和见习才能上岗。
截至2020年10月,现有的志愿者达700多人,其中热线接线员400多人。一名希望热线的工作人员透露,2017年,接线员有700多人,2022年,现有的接线员已不足300人。
这些接线员均为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老师、公务员、心理咨询师占大多数,业余时间接线。
2015年,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首期培训班,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很多人接线不久就走了,留在热线的只有120人左右。”
七年过去,李勇生估算,如今坚持留在热线的首批志愿者,不足20人。
人们离开的理由不一。有的因为工作调动,有的因为搬家,离得远了,有的结婚生了孩子,时间抽不出来。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高强度的输入和输出。李勇生说,从事危机干预的接线员,需要较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要不断地吸收知识,再进行大量的实践,是对精力的考验。
今年6月,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发布,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致辞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卫生危机,近10亿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李勇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城市的节奏加快,产生的伤感也越来越多,那些创伤和挫折,还来不及弥合,就有新的创伤填补进来。
他还遇见过热线依赖者——长时间依靠希望热线活着的人。“他们一空闲就打,也有一年打几十次,上百次的。咱从不问他姓氏,也不透露信息,但他一打进来,能听出我们的声音,说,是你啊。”
李勇生从不会让对方挂断,而是继续耐心倾听,“热线是这部分人群的希望,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他对热线这么依赖,说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打破,对他们是很大的创伤,我们能帮的话,还是会继续帮下去。”
对于庞大的自杀人数而言,热线仅是干预中的一环。它难以挽救如此多的有自杀意图的人群。
“光靠一个希望热线,真的是杯水车薪,心理咨询师本来就少,里面研究危机个案的就更少了。”李勇生说。
李勇生说,每个企图自杀的人,都会释放出自己的求救信号。“我们心理学叫三托六变,可能会发有托人托物托事的行为,并且在性情等方面会产生变化。”
一个细微的关怀,或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希望,就可能会挽回一个生命。“如果那时,我们刚好在他们身边,千万不要给他们再添加负担,只要做到一点,真正地支持他们,理解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不再变得那么孤独,就能有挽救的希望。”